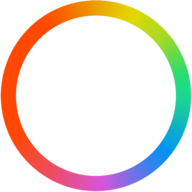2025年10月10日,一纸公告,再度让有棵树站在了风口浪尖:创始人肖四清正式离任,同时肖燕、唐仕莲、佘婵等核心管理层集体退出董事会,不再担任任何职务。
作为曾经叱咤一方的“华南城四少”之一,意外遭遇封号事故的有棵树曾一度走向濒临破产的末路,其能否在“内部大洗牌”后翻身,亦成为了行业当下关注的重点话题。

有棵树的这场权力争夺可追溯至2024年的破产重整程序。当年9月,在法院受理该公司重整申请后,由行云集团与纵控集团组成的联合投资人共同投入3.62亿元,取得重整后18%的股权,其中行云集团持有其中90%的份额。
作为行云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的王维,通过重整受让获得18%股权,成为第一大股东,而创始人肖四清的持股比例被稀释至不足3.3%。这种失衡的股权结构很快演变为控制权争夺。随后,董事会陷入否决循环,重大决议无法通过,公司治理濒临瘫痪。
2025年10月10日,有棵树召开临时股东大会,会议由王维方面召集,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占总股份的48.67%。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,由王维主持。在新一届董事会选举中,王维所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全部当选。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获通过,选举刘海龙为董事长,并聘任张文担任公司总经理。

▲图片来源于有棵树公告
此番变动并非普通人事更迭,而是一次彻底的“清盘”。肖燕、唐仕莲、佘婵等人均是伴随公司成长的核心决策层,他们的集体退出,标志着以肖四清为核心的创始团队对公司控制权的完全丧失,也意味着有棵树持续已久的内部控制权争夺战终于落下帷幕。

成立于2010年的有棵树,过去曾精准踩中跨境电商高速发展的时代风口。依托深圳完善的供应链体系,公司以家居建材、电子产品、航模配件为核心类目,2022年有棵树峰值SKU超百万,全球店铺总数近3900个。
这种“多平台、多账号、多品类”的运营模式,在行业处于流量红利期时展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。财务数据显示,2015年有棵树营收达10.78亿元,2016年半年即完成10.98亿元营收,全年营收24.86亿元,增速高达140.74%。鼎盛时期,公司年销售额突破50亿元,业务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但随着行业的发展,这种依赖单一模式与外部红利的发展路径逐渐落伍。2021年,有棵树被卷入声势浩大的亚马逊封号潮,损失惨重。据公开资料,2021年有棵树284个店铺被冻结,涉及资金超1亿元,直接引发连锁反应。2020至2023年间,公司累计亏损达44亿元。
在遭遇重创后,有棵树为挽救经营危局展开了一系列自救行动。
公司依托破产重整引入外部资本,并通过大幅削减研发投入、缩减人员规模等方式“节流”,力图维持基本运营。据调查,有棵树的研发费用从2022年的1100万元骤降至2024年的152万元,人员规模缩减75%。
此外,2024年12月有棵树新设立长沙湘树云和长沙悦云树公司两家子公司,目的为“引入业务资源,开拓新兴市场”。
在有棵树2024年财报中,对2025年度经营计划是:依托重整投资人提供的资本性投入与产业投资人承诺的产业性资源,对公司跨境电商出口业务进行赋能;督促牵头产业投资人逐步向上市公司注入进口业务,实现优质产业在长沙落地。
从中,可以看出有棵树对发展跨境电商业务的决心仍然十分明确,正准备推出一系列措施实现转型升级。
然而,深入观察发现,其自救努力尚未触及根本矛盾。尽管提出“依托产业资源赋能”和“注入进口业务”的战略愿景,但新设子公司的经营类目仍涵盖食品、化妆品、电子产品乃至汽车配件等跨境电商全品类。这一产品布局清晰表明,其业务模式仍未走出依赖SKU海量覆盖的传统“铺货”逻辑。
而且,直到2025年公司仍深度依赖第三方平台,根据2024年半年报,来自Shopee的收入为5172万元,是公司第一大收入平台。来自亚马逊的收入为3878万元,是公司第二大收入平台。
这种转型不彻底性直接反映在经营成果上。根据2025年半年度报告,有棵树营业收入同比下滑81.33%至4257.34万元,虽然实现归母净利润187.70万元,但扣非后净利润仍亏损899.93万元。在公告中,有棵树坦言,其“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,公司自身造血能力仍未恢复”。
这个行业已经从“人人都能赚钱”的普惠红利时代,进入“品牌赚溢价、细分赚红利、铺货赚辛苦钱”的分层时代。
对于跨境电商从业者而言,有棵树的兴衰史既是一个警示,更是一面镜子。当行业告别草莽,走向成熟,唯有那些能够快速适应变化、深耕细分领域、建立品牌价值,并持续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卖家,才能在新浪潮中行稳致远。